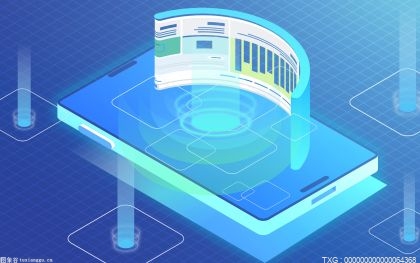提起草根代筆_草根什么意思 大家在熟悉不過了,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,那你知道草根代筆_草根什么意思 嗎?快和小編一起去了解一下吧!
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草根代筆(草根是什么意思)
世界很遠(yuǎn),生活很近。
時(shí)間長,時(shí)間短。
還有空,過來聊聊。
聊江湖故事,看風(fēng)暴卷,
世界很大,我們?nèi)タ纯窗桑?/p>
事情比較復(fù)雜,簡單說一下吧。
歡迎,我們聊聊。
大年三十,我用手機(jī)視頻安慰江蘇南通的老人:“今年 *** 號召我們?nèi)ズ贾葸^年,春天我就回家看你。”
老人慢慢地點(diǎn)點(diǎn)頭,然后問道:“前幾天不是春天嗎?”
我心里一顫,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話。老人也是90后:過完年就九十五歲了。
來源:視覺中國
一個(gè)
我對中國詩歌始祖《擊地之歌》情有獨(dú)鐘: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掘井而飲,耕田而食。帝力能拿我怎么辦?”
近一個(gè)世紀(jì)以來,這似乎是我父母生活的真實(shí)寫照。
往南30多里是長江,往東60多里是黃海。這片長江和黃海交匯處的蘇北平原是我的故鄉(xiāng),我世代在這里務(wù)農(nóng)。
按照現(xiàn)在的標(biāo)準(zhǔn),我家老頭子就是個(gè)手藝人,也有點(diǎn)手藝人的味道。只要風(fēng)調(diào)雨順,國富民安,他自己能行,全家都能豐衣足食。
20年前,他還沒老的時(shí)候,做過設(shè)計(jì)師、監(jiān)理、施工員。我的父親和兒子可以建一棟房子。
老人可以是木匠,泥水匠,畫家,竹藝工匠。有了這四樣手藝,再加上三四個(gè)幫手,建一個(gè)磚木結(jié)構(gòu)的農(nóng)家樂并不難,更不用說瓦爾登湖邊的原木民宿了。
我還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學(xué)會(huì)這些技能的。那不像現(xiàn)在。嗶哩嗶哩和Tik Tok有木工教程。悟性好的還是能畫葫蘆的,也能有所作為。
現(xiàn)在的孩子一邊學(xué)編程,一邊學(xué)木工;白領(lǐng)們擺好木匠的工具,學(xué)做手工,是一種時(shí)尚。
曾幾何時(shí),在我們家,普通的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,做工精細(xì),樣式規(guī)整,但沒聽說過他拜過老師。
吳鵬,祖祖輩輩在斯里蘭卡耕耘的故鄉(xiāng)。
大三的時(shí)候,我需要一個(gè)木箱。我父親花了兩天時(shí)間打了一個(gè),用黃色油漆涂上去,和專業(yè)木匠做的沒什么區(qū)別。
那年暑假剛開始,我從揚(yáng)州長途汽車站下了車,去學(xué)校的車上人很多。司機(jī)不讓我上,我就提著箱子走了三四里路到了大學(xué)宿舍。
來源:視覺中國
這個(gè)盒子我大學(xué)用了兩年,去杭州讀研的時(shí)候又用了三年。現(xiàn)在我是老人自己的收藏箱。
當(dāng)然,老人的手藝還不止這些。家里的洗菜筐壞了,他就去屋后的園子里砍些竹子,用木刀砍,一天就能砍完。
需要一個(gè)“怒風(fēng)”燈,他買了幾塊玻璃和鉛皮,不到半天就能搞定。從盛夏到初冬,我們晚上釣魚抓螃蟹,我和弟弟一直帶著。
有一次耳朵癢了,他隨手找了一根粗鋼絲,鍛造了一把挖耳勺。
這是個(gè)小玩意,但卻是個(gè)精致的作品。它是用鐵錘和鐵砧手工建造的。至少三十年過去了,現(xiàn)在還閃閃發(fā)光,還能用。
我的家鄉(xiāng)是典型的魚米之鄉(xiāng)。有了這些技能,再加上農(nóng)活的輕松,我自給自足有余。
蔬菜種在地里。如果你想吃肉菜,河里有很多蝸牛和河蚌。捕蝦有點(diǎn)難,但是家里隨時(shí)都有捕蝦的魚竿和網(wǎng)袋。有一天,當(dāng)你的嘴有點(diǎn)蒼白的時(shí)候,你們都可以去河邊轉(zhuǎn)轉(zhuǎn)。
上世紀(jì)80年代初,農(nóng)村并不富裕,但大人干活,小孩玩耍,人們到處歡呼,這是典型的社會(huì)主義新農(nóng)村景象。
我常常想,現(xiàn)在推進(jìn)鄉(xiāng)村振興,除了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發(fā)展,首先要恢復(fù)的是30年前農(nóng)村的熱鬧景象。
二
來源:視覺中國
我父親接受的是老式教育,大概是在20世紀(jì)30年代。
他熟悉四大名著中的許多典故。我很小的時(shí)候就知道人生三惡:德行弱但威望高,智慧小但野心大,實(shí)力小但責(zé)任重。
那時(shí),我還不認(rèn)識(shí)南·懷瑾。易經(jīng)中的這段話是受了老人的啟發(fā)。
如果日本鬼子沒進(jìn)來,老人的中學(xué)教育別無選擇,只能中斷。他和我們家族的歷史是否會(huì)被改寫還不確定。
當(dāng)然,他不可能上大學(xué),也不可能上西南聯(lián)大。我查了一下,當(dāng)年的大學(xué)學(xué)費(fèi)太貴了,大部分農(nóng)民都不敢奢望。我爺爺家家境殷實(shí),但也就幾畝地,一頭牛是幾個(gè)兄弟的共同財(cái)產(chǎn)。
上世紀(jì)二三十年代,中國農(nóng)村的文盲率超過80%,我的父母不會(huì)讀書寫字的人也不多,所以我父親有一項(xiàng)義務(wù)性的工作:為別人讀書寫信。
到了七八十年代,村里風(fēng)氣逐漸開放,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外面參軍、工作、學(xué)習(xí)。當(dāng)他們回來時(shí),他們的父親帶來了這封信,并讓我父親閱讀。看完回復(fù),請爸爸給我寫。
冬天昏暗的油燈下,一家人圍坐在一起,我媽縫縫補(bǔ)補(bǔ),我們做作業(yè)。父親戴著老花鏡喃喃自語,一副小心翼翼的表情,頗有賈島月下深思熟慮的味道。
我讀書十八年,文憑比父親高,斷斷續(xù)續(xù)練了幾年書法,卻一直沒人介紹。父親每次看到我寫字都微微搖頭——我跟他差太遠(yuǎn)了。
我是學(xué)歷史的,父親有興趣也會(huì)和我探討一些話題,但是我發(fā)現(xiàn)他的很多歷史知識(shí)都是來自傳統(tǒng)戲曲。
比如他的封神榜和楊家將的知識(shí),跟后來單田芳講故事一模一樣。楊家將的《四郎探母》和京劇中的《金沙灘》等。,都是他能哼出一段的底細(xì)。
除了給別人寫信,每年春節(jié)他還有一個(gè)套路:給鄰居寫春聯(lián)。他的楷書技藝不亞于我見過的很多業(yè)余書法家,但他沒靠這門手藝賺過一分錢,家里也沒有一幅自己的墨寶。
三
來源:視覺中國
我父親曾經(jīng)是個(gè)老煙槍,他有一個(gè)多年的習(xí)慣:每天晚上睡覺前,他都坐在床上抽一根煙。他的母親經(jīng)常若有所思地嘮叨這件事,但他從不回應(yīng)。
有一年冬天,他騎車經(jīng)過門前的小石橋,結(jié)冰的橋面打滑。他甚至把自己的車和人摔在橋下的冰上,摔斷了腰和腿。
在醫(yī)院簡單治療后,老人回家躺下了。全家人都很擔(dān)心,我們甚至做好了他可能從此臥床的準(zhǔn)備,但半年后他奇跡般地康復(fù)了,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
更不可思議的是,從那以后,他戒煙了,沒有掙扎,沒有重復(fù)。那時(shí)他將近70歲。
幾年后回想起來,父親的戒煙是可以避免的。那年哥哥因病去世,年僅48歲。父母突然變老,母親開始彎腰駝背,本來就沉默寡言的父親也從此少言寡語。
八十歲的時(shí)候,老人毫無征兆地戒酒了,這是他很小的時(shí)候就養(yǎng)成的習(xí)慣。他一天吃兩餐,一天兩兩餐。
七八十年代,農(nóng)村好像什么都能釀酒,高粱酒不太好喝。而地瓜干甚至印楝果做的白酒,又粗又燙,喉嚨里像冒煙,比現(xiàn)在的諸暨銅山燒路,號稱江南茅臺(tái),要大得多。
現(xiàn)在洋河酒廣告鋪天蓋地。那時(shí)候一兩瓶是高檔貨,連莊稼人都買不起。
五六十歲之后,隨著體力的下降,這位技術(shù)嫻熟的老人的主業(yè)逐漸清晰:綁掃帚。對他來說,這是一門沒什么難度的手藝。
我的家鄉(xiāng)有取之不盡的高粱稈和蘆葦花。他干活很慢,他的掃帚又漂亮又耐用。
在鎮(zhèn)上的集市上,賣掃帚的老人姓吳。除了我老頭子,我還有幾個(gè)遠(yuǎn)房叔叔,他們建立了行業(yè)標(biāo)準(zhǔn),掌握了定價(jià)權(quán)。
有幾年,每把掃帚的價(jià)格是三元,后來通貨膨脹嚴(yán)重,調(diào)整到五元,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考慮到原材料和人工成本,工藝水平,我一直覺得這個(gè)價(jià)格不可思議,拼多多再怎么努力也拼不出這個(gè)價(jià)格。
媽媽說他綁掃帚不是為了錢。我非常理解我的父親。他耳朵不太好,然后視力差,不愛說話。做這些手藝和在城市里放松是一回事,只是為了打發(fā)時(shí)間。
每隔兩三天,他就騎著這輛有20年歷史的永久牌自行車去鎮(zhèn)上賣掃帚,直到太陽落山。
老人創(chuàng)造的東西,別說用過的人,就是見過的人,都是有口皆碑,質(zhì)量上乘的。唯一的問題是他出手慢,輸出不高。
四
老人91歲的時(shí)候下田伺候菜地。吳鵬攝
這位老人是個(gè)慢性子,做什么都慢吞吞的。我媽媽經(jīng)常批評他反應(yīng)慢。現(xiàn)在我明白了,這就是工匠精神,在當(dāng)代是珍貴而稀缺的。
無論我媽怎么嘮叨,老人很少生氣,甚至很少不說話。
每次假期開始,父親大多推著我的自行車去鎮(zhèn)上的車站,一路上幾乎沒什么話可說。我上車,車慢慢啟動(dòng),他慢慢轉(zhuǎn)過身。當(dāng)我讀到朱自清的背影時(shí),我感覺我是在寫我的父子。
我上大學(xué)的時(shí)候,父親保持了半個(gè)月給家里寫信的習(xí)慣,給我講村里的家庭情況,我也給他們通報(bào)學(xué)校的情況。書信的字跡很工整,書信的措辭也和古人差不多。
這位老人也喜歡看書。前幾年郵寄書籍,送貨地址默認(rèn)成了老家。過年回家,他說書挺好的,就是不好讀,字小。
這是一本純粹的學(xué)術(shù)書籍,研究中國古代朝貢制度的演變。我們家的其他人不感興趣。
他對國學(xué)和傳統(tǒng)的東西感興趣,但他不喜歡看電視。聽收音機(jī)主要關(guān)心天氣預(yù)報(bào)。
最近二十年,對于我父親這一代人來說,時(shí)間似乎靜止了。他們不知道世界的變遷。老人不懂 *** ,不會(huì)用手機(jī),近幾年耳朵眼睛都不聽他的了。他不會(huì)讀書看報(bào),天生不愛聊天,所以越來越沉默。
五
來源:視覺中國
這位老人,生于20世紀(jì)20年代初,經(jīng)歷了近百年。在足不出戶就知道世界的時(shí)代,他的技術(shù)已經(jīng)沒有用了。
可惜二三十年前,農(nóng)村缺乏文物保護(hù)和收藏的觀念,老人也是。家里那些鍋碗瓢盆都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,有幾百年的歷史了。
那些雕花門窗和今天烏鎮(zhèn)、周莊的一樣,但是隨著房屋的改造,早就不見了,更不用說做工藝品的工具了。
90年代初,外地人來村里買舊家具,舊瓷器之類的,用很低的價(jià)格到 *** ,里面大概有清朝甚至明朝的古董。
現(xiàn)在家里有一個(gè)裝著針和針的竹籃,是我奶奶傳下來的,她已經(jīng)去世快四十年了。
幾次拆房子, *** 的木匠、泥水匠、油漆工、竹編工、紡車、織布機(jī)、織襪機(jī)等。,都不見了,連鋤頭之類的農(nóng)具也越來越匱乏。
有些東西,從我爺爺那一代,到現(xiàn)在也算是文物了。它們被放在城市里,可能會(huì)進(jìn)入博物館。如果是名人或者革命家庭,在革命歷史博物館是給游客參觀的,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素材。
六
比這些現(xiàn)實(shí)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的消失更讓人難過的是精神文化遺產(chǎn)的褪色。
經(jīng)歷了百年滄桑的老人,本身就是百年孤獨(dú)史。清末實(shí)業(yè)救國狀元張謇故居,離我老家不到二十里。
抗日戰(zhàn)爭時(shí)期,我的家鄉(xiāng)以河為界,新四軍與偽軍、國軍、日軍斗爭。情況極其復(fù)雜。
對我們來說,這些都是歷史,但對老人來說,要么不遠(yuǎn),要么自己經(jīng)歷過。上小學(xué)的時(shí)候,老人偶爾會(huì)口述給我們聽,后來我們沒問,他就沒再提了。
十幾年來,農(nóng)村調(diào)查和口述歷史非常流行。作為歷史專業(yè)人士,我沒有要求父親好好交代。這是浪費(fèi)時(shí)間。我對家族歷史知之甚少。
這位老人,以前是個(gè)手藝人,抽不出時(shí)間,經(jīng)常感嘆自己老了,什么都干不了。我找不到話來安慰他,但我感到沮喪。
每次回來,爸媽都迫不及待地把種在地里的植物都裝進(jìn)樹干里。吳鵬攝。
去年,我91歲的母親,我父親70年的妻子,在癱瘓一年半后去世。燒飯后的之一天晚上,我和爸爸歇腳坐在床上。他很認(rèn)真的對我說:記住你媽媽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和時(shí)間。當(dāng)他說這話時(shí),我淚流滿面。
這位老人的余生一直保持著超然的態(tài)度,不愿意向別人求助,也不愿意向別人求助,包括自己的孩子。
住在我老人家就像長江,從野古而來,到我家南邊,靠近河口,波光如鏡,江面明如天。無論多么狂風(fēng)暴雨,雷霆萬鈞,都在我們身后,都是歷史。
來源:視覺中國
本文為錢江晚報(bào)原創(chuàng)作品。未經(jīng)許可,禁止轉(zhuǎn)載、復(fù)制、摘抄、改寫及在網(wǎng)上傳播所有作品,否則,本報(bào)將通過司法途徑追究侵權(quán)人的法律責(zé)任。
關(guān)鍵詞:
責(zé)任編輯:Rex_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