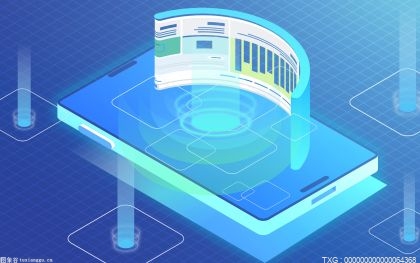“長白雄東北,嵯峨俯塞州。迥臨滄海曙,獨(dú)峙大荒秋。”清代詩人吳兆騫寫盡了長白山的雄偉壯麗,也讓人知道了它的險(xiǎn)峻荒涼。一輩子堅(jiān)守這里,在普通人眼里是多么艱難不易,可在吉林通化工務(wù)段橋隧車間第一維修小組組員的心中卻是那么甘之如飴。
春防融雪落石、夏抗酷暑洪澇、秋除枯枝倒樹、冬戰(zhàn)嚴(yán)寒冰雪。幾十年過去了,盡管環(huán)境艱苦、終日奔波,但第一維修小組里從未有人申請離開。他們說,如果再有選擇職業(yè)的機(jī)會(huì),還會(huì)選擇沿著鐵路線巡檢。對這份別人眼中的苦差事,他們一生愛一次,一次愛一生。
 (資料圖)
(資料圖)
“兵哥哥”成了“冰哥哥”
第一維修小組共13人,其中9人在部隊(duì)扛過槍,是群名副其實(shí)的“兵哥哥”。
冬季的長白山天寒地凍、滴水成冰。鐵路線上的涵洞、隧道不斷積雪積冰,如不及時(shí)處置,冰層增厚會(huì)直接影響列車安全。“兵哥哥”沒日沒夜和冰打交道,真就成了“冰哥哥”。
老嶺隧道,是整個(gè)梅集鐵路線上最長的隧道,全長2323米。由于年代久遠(yuǎn)、設(shè)備老化,一到冬季,隧道側(cè)壁和拱頂?shù)牧魉紩?huì)形成冰柱。每年從11月開始到次年4月,第一維修小組要輪流看守隧道,視結(jié)冰情況定時(shí)打冰,不分晝夜,一干就是半年。
冬季凌晨2點(diǎn)是結(jié)冰長勢最猛的時(shí)候,守隧的“兵哥哥”穿上厚厚的工裝,拿上作業(yè)工具,走進(jìn)隧道。深夜的隧道,漆黑一片,陰寒噬骨。借著手電筒和頭燈,他們仔細(xì)檢查隧道側(cè)壁和拱頂。側(cè)壁上有冰柱,就用鐵鎬刨;拱頂上有冰層,就用打冰桿打。打掉的冰碴、冰塊還要裝進(jìn)袋子里扛出去。裝滿冰的袋子有30多公斤重,一次打冰作業(yè)最少要扛二三十袋,多時(shí)要扛六七十袋,每個(gè)人都累得氣喘吁吁、渾身是汗。
梅集線159公里涵洞處也是每年冬季重點(diǎn)防守的地段。涵洞在小山溝里,重型機(jī)械上不來,“冰哥哥”們只能靠人工除冰,有的地段狹窄,還得貓著腰干活。10米長的涵洞,冰層堅(jiān)硬似鐵。幾個(gè)人輪流用電鎬砸冰,飛濺的冰碴崩打在護(hù)目鏡上和臉上啪啪作響,臉頰瞬間泛紅、掛滿冰水,衣服上也濺滿泥漿,很快就凍成一身“冰甲”,走起路來,嘩嘩作響。
“這冰1小時(shí)能長10多厘米,不及時(shí)清除就會(huì)影響列車運(yùn)行安全。”工長劉傳雙說,冬天,就是和積冰賽跑,必須在規(guī)定的時(shí)間內(nèi),把冰清理干凈,才能消除隱患。每個(gè)冬季,“冰哥哥”們從橋梁底部、涵洞內(nèi)部、隧道內(nèi)清理出的積冰,累積起來有1500多立方米,差不多一個(gè)游泳池。
最大的考驗(yàn)是“烤”驗(yàn)
盛夏8月,烈日炎炎。鐵軌上熱得可以煎熟雞蛋。
一靠近梅集線127公里282米處的第一渾江鋼梁橋,就感到一股熱浪迎面撲來,整個(gè)鋼梁橋就像是一個(gè)露天的“烤箱”。
為保障橋梁安全,第一維修小組每月需對橋上908根枕木、606個(gè)護(hù)木螺栓以及1816個(gè)鉤螺栓和支座全面檢查,每3個(gè)月進(jìn)行一次保養(yǎng)。
烈日下作業(yè),他們早已習(xí)以為常。利用施工“天窗”時(shí)間,大家分工協(xié)作,拆除被腐蝕的護(hù)木、放上新護(hù)木、上好護(hù)木螺栓……
中午時(shí)分,軌溫接近50攝氏度。頭上是如火的太陽,腳下是滾燙的鋼軌,承受著雙重“烤”驗(yàn),幾分鐘就會(huì)汗如雨下。可是要對鋼梁橋零配件進(jìn)行記名式檢查,還要全面復(fù)緊2422個(gè)鉤螺栓和護(hù)木螺栓,全套作業(yè)下來,至少四五個(gè)小時(shí)。
高空作業(yè)的“小荒溝”塢工橋檢查難度更大。“90后”班長王宏志系上安全帶,踏上檢查梯,一手抓緊旁邊的扶手,一手拿著工具,仔細(xì)檢查礅臺(tái)支座螺栓有沒有松動(dòng)、梁底有無裂紋。高溫下,懸在50多米空中作業(yè),不一會(huì)兒便全身是汗、渾身酸疼、手腳發(fā)麻。
“王胖兒,快下來,我們干會(huì)兒。”每到這時(shí),組員都會(huì)大聲地喊,搶著系上安全帶替換他。
人,一撥一撥地?fù)Q;活,有條不紊地干。說不清多少汗水滴落在鋼軌上,一眨眼兒就干了。
“守隧人”守歲
老嶺隧道口有座小屋,是第一維修小組組員巡檢作業(yè)休息時(shí)的巡守房,也是職工們的第二個(gè)“家”。“家”不大,30平方米,可是夠溫馨。每年元旦和春節(jié),“守隧人”在這里守歲。
守歲很有儀式感,門上要貼春聯(lián)、福字,炕上要擺水果、瓜子、花生和糖,桌上要有雞鴨魚肉,但餃子得第二天早上吃,因?yàn)槟耆畠和砩希麄冋諛右ニ淼来騼纱伪L烀擅闪恋臅r(shí)候,打冰的隊(duì)伍回來了。劉傳雙和宮汝文已經(jīng)包好了餃子,灶臺(tái)上大鍋冒著熱氣,爐膛里的柴火噼啪作響。
熱騰騰的酸菜肉餡餃子剛端上桌,趙若明的手機(jī)鈴聲響起,打開手機(jī),兒子出現(xiàn)在視頻里,“爸爸,你3年沒回家過年了,媽媽怕你吃不好,煮了螃蟹和大蝦,一會(huì)給你送去。”
“老公過年好,祝你們和隧道都平平安安!”妻子趴在兒子肩膀上笑著說。
“謝謝媳婦!”平日里的鋼鐵漢子,一下子兩眼泛紅。藏在心里的那個(gè)字,還是沒有說出來。
(松花江網(wǎng)編輯 楊世陽)
關(guān)鍵詞:
責(zé)任編輯:Rex_02